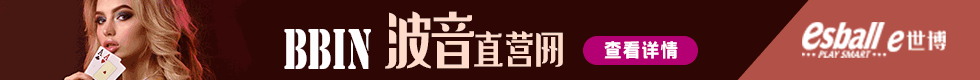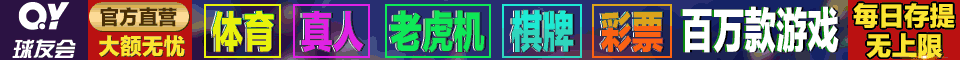你的位置:网上棋牌游戏 > 真人保险楚汉德州游戏 >
这个活动看起来倒是搞得五彩缤纷的在线棋牌
发布日期:2024-05-07 13:41 点击次数:175(第七章/1)
寂寞时的爱
“就像冬天的刺猬一样依偎着互相取暖,靠得太近了会彼此伤害,离得远了又无法忍受世间的严寒。
”
——罗叔卡博《爱情的起源》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学生活的一切事务都是围绕着恋爱来展开的。
一起逃课可以让你们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稳固,名家大师的讲座会让你们对某个冠冕堂皇的话题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和看法,社团活动给你们的恋爱加入一些恰到好处的猜忌和嫉妒,至于漫无边际的暇闲和宽松的环境则是你们纵情欢愉的温床。
别人眼里的大学生活是不是显得更加丰富和深刻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纵乐败坏的源由。
或许我们天生都是现实的享乐主义者,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色彩鲜明地开始了我们道德败坏的一生。
几乎看不到任何质朴的品德在大学校园里得到肯定和实践。
克制、勤俭、厚道,这些仿佛成了令人蒙羞的标致,我们尽可能地避免和它们发生任何关联。
确切地说一切都在朝着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们总是侃侃而谈讨论一些时髦光鲜的理论,比如移动互联网或者金融战争;我们极力让自己的行头看起来更光亮些,哪怕只是些冒牌货也能取得心理上的相对优势;我们甚至避免接触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比如诗歌。
所以当叶子才真的搞了个现代诗歌社团时,我倒对那小子刮目相看。
虽然我知道他搞这个什么鬼“鹿鸣社”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借用一个高雅的名头来网罗文学院一批外貌可人的女生时常出来进行一些私人性质的聚会,但这至少相对那些公开宣称以玩乐为目的社团来说还算是含蓄的。
在赵子才几番挑衅式的邀请下,我只得加入了他们的鹿鸣社。
一来顾海抑郁休学后我所能交流的人几乎没有,二来我也想通过一些不太过火的社交活动来冲淡别人对我的成见。
倘若我还是成天窝在宿舍研究百家乐,早晚会被人当成神经病告发到学校。
大学这种地方虽说自由,但这种自由也只是徒俱其表罢了。
你逃课或者乱搞男女关系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你若对大家都十分热衷的社团活动完全无动于衷而一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那么你总是会被种种猜疑和不怀好意的目光所冒犯。
归根到底大家都是不学无术,内心多少还是有点惶恐的,所以全都希望大家都一样地流于表面敷衍应对就皆大欢喜了。
(第七章/2)
恩,我加入鹿鸣社没多久,刚好碰上这个社团成立一年的纪念活动。
就此,世界杯期间竞彩的销量冲刺画上了一个结点。那么,本届世界杯期间竞彩的总体销售表现具体如何?我们一起来回顾。
叶子才通知所有社团成员准备一首自己的原创的诗歌以便举行一个诗歌朗诵的活动来纪念社团成立一年。
这个活动看起来倒是搞得五彩缤纷的,有古文诗词,有外语诗歌,也有各种打油搞笑的无厘头作品。
说起来倒也奇特,文学院里面虽然有一半以上的人连罗叔卡博的名子都没怎么听过,可一谈到现代诗歌却个个说的头头是道。
其实在我看来汉语现代诗歌大多只是实验之作,虽然也不乏亮点,但毕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若靠看这些东西来提升文学鉴赏和创作能力,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
林秋宜作为叶子才的女朋友理所当然的成了鹿鸣社的副社长,当然也可能是她成为副社长后投桃报李地成了叶子才的女朋友也未可知。
总之他们两个一唱一合倒也把这个社团搞得有声有色。
说起来叶子才这小子泡妞倒真有一套。
正因为他女朋友是副社长的缘故,其它女生反而更加容易亲近并加入鹿鸣社,而且还有好几个蛮漂亮的女生为他争风吃醋。
作为主角他自然占尽便宜并趁机四处卖乖讨好。
入学一年多,看惯了这些朝秦暮楚落花流水的事情后,我对叶子才倒也没那么反感了。
他只不过也是在逢场作戏罢了,只是他比一般人更敬业入戏更深一些。
就敬业这点来说。
我确实很佩服他。
他选了电子商务作为第二专业,同时他英文也非常棒,跟几个外教混得很熟。
而我则在大二把英语六级过了后就彻底按自己的那一套来搞了。
我他妈的才懒得管什么学分,什么保研,什么就业。
总之自己喜欢什么就鼓捣什么。
我的底线是各门功课都及格。
我做到了,一次也没挂科。
我懒得重考。
话说大二暑假从澳门回来后我大部分时间依然窝在宿舍沉迷于百家乐——我通过网络购买到两本从港台翻印过来的百家乐专著《五局八星》和《百家乐数理分析》——完全没把鹿鸣社诗歌朗诵活动放在心上。
待到活动马上要举办的当天,我才想到自己也得准备一首诗歌来应对才行。
其实我高中时也写过一些诗歌作品,但现在看来那都只不过是些临摹之作,读起来自己都觉得羞愧。
我本想把最近给顾海回信时写的那首《登岳麓山访故人墓》拿出来充一下门面,可是一想到广东这边的学生对历史和地理近乎一无所知,也就只能作罢,免得自讨没趣。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把顾海的那首《抑郁症》背熟了拿去应对。
(第七章/3)
诗歌朗诵在水库边学术交流楼的裙楼里举行,依山面湖,视野显得相当开阔。
让人不得不打起点精神的是叶子才居然把校基金会的董事和文学院的客座教授也请了过来,此外他还纠结了一帮搞摇滚音乐的家伙前来助兴。
坦白说他的组织运筹能力我辈这种书呆子真是望尘莫及。
活动开始时叶子才煞有介事地来了一通开场白,大意是说要通过鹿鸣社来保持我们对诗歌的敏感和热情,并希望这个社团在文学院一直传承下去。
如此云云。
然后他怀着十二感激之情请校董和客座教授发表讲演。
校董毕竟是校董,他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探讨了诗歌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问题。
最后他期望S大的学子能出一些在国际诗歌节上拿奖的作品以光耀门楣。
当然他的原话并没用光耀门楣这个词,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为此他说了有十几分钟。
客坐教授则用英文朗诵了一首聂鲁达的诗,然后又用英文简单阐述了一下他对这首歌的看法。
这哥们是个美籍华裔他用英文表达倒也没什么不妥,事实上S大很鼓励双语教学。
但问题是聂鲁达的原著是西班牙语的他却用英语来阐叙它。
他的逻辑让人很难接受。
也许他是故意的。
那些搞文学的总是喜欢在逻辑上乱来,以便体现自己能受到他人额外豁免的优越感。
所以很多时候我不太喜欢那帮子专门搞文学的人。
我倒更喜欢那些不是专门搞文学的人偶尔搞一下文学。
接下来鹿鸣社的成员依次朗诵了自己的诗歌。
叶子才抄了首勃洛克的抒情诗,朗诵起来声情并茂、理直气壮。
其它大部分人也是如法炮制,要么明抄,要么暗仿,听起来都像那么个调调——现代诗歌令人头晕目眩的虚晃感。
你若问他这诗到底要表达些什么,他们多半说不上来。
我在倒数第二个才上场,当时校懂和客座教授等嘉宾早已经匆忙离场。
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将顾海那首《抑郁症》念完。
这会我突然觉得顾海休学实在是明智之举,至少不用勉强卷入这些故作姿态的社团活动。
我念完诗后台下一点反应都没有,仿佛我念的根本不是诗,而是示波器使用指南之类的玩艺。
最后林秋宜站起来带头鼓掌,但其它人——几乎全部是女生——并没有被她的行为所带动,她只好尴尬地朝我点头笑了下。
显然她对顾海这首诗还是有点感触的,对此我多少心存感激。
我打心眼里希望这个世界能多一些人接纳并喜欢顾海那样的人。
诗歌朗诵完后大家都嚷嚷着去食堂一起吃宵夜,我只得在前往食堂的路上找了个机会溜回宿舍。
我在想自己这一天到晚的都在干些什么事呢。
我突然觉得人这一生未免太过漫长和枯燥。
若是如此日复一日,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要是能有一场博弈让我跟这种岁月分个胜负,我会毫不犹豫地押上自己所有的一切。